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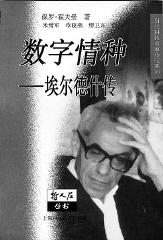
2000多年前,在印度有个哲学学派———数论派,以一部《数论颂》传世。20世纪也有一部博大精深的“数论颂”,作者都是些不朽的天才:希尔伯特、哈代、维诺格拉多夫、西格尔、怀尔斯等等,当然还有《数字情种》的主人公保罗·埃尔德什(PaulErd s)。
在1996年9月召开的一次学术会议上,埃尔德什因心脏病突发结束了其83岁的漫长一生。1999年3月,美国著名的《时代》周刊将埃尔德什列为20世纪四五十个头脑强人之一,和哥德尔、拉马努金并列为20世纪三个数学奇才,并提到他有485个合作者的世界纪录。
埃尔德什是匈牙利数学家。20世纪初,就在匈牙利这个小国里诞生了一大批优秀科学家,最有名的当然是冯·诺伊曼。埃尔德什比他小十岁,1930年代已在数坛崭露头角。为了逃避希特勒的迫害,埃尔德什开始周游世界,不料这个习惯保持终生。他是一个一无财产、二无妻小、三无居所的“三无”人员。看着他拎着旧包走在路上,不认识的人怎会知道他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离散数学家、沃尔夫奖获得者呢?埃尔德什自己则根本不在乎,在他心目中,数学远远高于物质世界。
通常情况是,埃尔德什跨进一位数学家的大门,宣布“我的头脑敞开着(Mymindisopen.)”,然后就和别人展开研究。临走时,则说“另一个屋顶,另一个证明(Anotherroof,anotherproof.)”数学家的话也有惊人的反例:据说有一次在火车上,埃尔德什与一名列车员合写了一篇论文!埃尔德什把分分秒秒都用于数学研究,他一生参与了1475篇论文的写作,而且篇篇都有分量,他是20世纪的欧拉。
从1980年代起,西方数学家和记者写了大量文章介绍埃尔德什的传奇经历和卓越贡献,但《数字情种》仍包括了大量鲜为人知的故事,比如:埃尔德什与爱因斯坦、哥德尔、哈代的交往,和乌拉姆、格雷厄姆的友谊,也有他在德国法西斯猖獗时的处境,对美国苏联的政治见解;为什么讨厌异性、喜欢小孩以及其在生活中不计其数的趣闻逸事。读来让人忍俊不禁。埃尔德什是纯粹数学家,但《数字情种》却处处体现了一个活生生的人的形象。许多人喜欢埃尔德什,就像喜欢费恩曼一样。因为这两人不仅幽默风趣,极具个性,而且讨厌虚伪,热爱真理(虽然在许多方面两人很不一样)。费恩曼打动了格里宾,埃尔德什则打动了保罗·霍夫曼———一个有地位的出版商和记者。霍夫曼心甘情愿地伴随埃尔德什度过了最后十年,写下了畅销书TheManWhoLovedOnlyNumbers,中译本就是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哲人石丛书·当代科技名家传记”中的新品《数字情种》。
正如“爱情是文学永恒的主题”,自然数是数学永恒的课题。数带给人们的认识是一种“确定性复杂”,而使人们充分认识到这种复杂性的,笔者以为埃尔德什是头号功臣。
大家知道,欧几里得几何的公理是完备的,无论多难的几何题,都是必定能做到底的。用现在的时髦话说,就是:欧氏几何的所有命题都是可判定的(非对即错)。
数的本质大为不同,大概它太基本了,人们曾低估了其复杂程度。直到1930年,哥德尔证明了一条著名的定理:一个包含初等数论的形式系统必定是不可判定的。这个以哥德尔不完全性定理著称的结论大大出乎人们的意料,它暗示数的复杂程度和欧氏几何的复杂程度不在一个数量级上。
埃尔德什使人们充分认识到了数学中惊人的复杂性。一般人们认为,数学既不涉及时间也不涉及人,总比物理学、生物学“简单”。《数字情种》却告诉我们(这正是埃尔德什的观点),数学远为支离破碎。数学的研究对象是开放的、无限的,工具随时都可能不够用。要解决一个貌似简单的难题,数学家必须引进一大堆“复杂得多”的新工具才可能奏效。比如怀尔斯证明费马大定理就是一个典型例子。如果谁想用比较初等的工具给出新证明,难度当然更大,也很有价值,因为新工具固然对推动数学发展起很大作用,建立老概念和老方法之间错综复杂的有机联系,也是数学的重要任务和鲜明特色。埃尔德什本人确也提供了一个全部数学中最著名的例子。那是在1949年,他和塞尔伯格用初等方法(当然很复杂)首次证明了素数定理(高等证法在1896年给出),推翻了哈代的观点,在世界数学界引起极大轰动。
与数学完全类似,心理学也存在对复杂性的需求。在病人心目中,心理医生与其平易近人,还不如做得像一尊神,他的教诲应该充满隐喻、暗示和跳跃,有点像禅宗、密宗或量子力学,让病人感到医师比自己更深广、更复杂、也更神奇,从而对其充满敬畏。当然,心理学家的做法并不是搞伪科学或反理性。像荣格或弗洛伊德这样伟大的心理学家承认心理学是科学,是服从理性的。但这种理性的复杂程度可想而知,它肯定不是笛卡几的“我思故我在”,而是一种更“高阶”的理性。这种高阶理性可能就是印度数学奇才拉马努金的思考方式。埃尔德什毕生对拉马努金充满敬仰之情,曾拿出许多钱资助拉马努金的遗孀。
复杂性对于人类的意义在于:人们不是要战胜复杂性,而是力求驾驭复杂、利用复杂。国际象棋是另一个著名例子。数学上早就证明:对于国际象棋,先走者有必胜或不败策略。这种策略一旦找到,国际象棋也就“寿终正寝”了。好在国际象棋是足够地复杂,以至于像卡斯帕罗夫在走出几十步后也感觉不到先走的优势。至于理解自然数的复杂性,当然更有意义,比如著名的RSA公钥密码制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因为大的殆素数因子分解很复杂,所以利用这种数制造密码,就可以让敌人一筹莫展。埃尔德什对因子分解很有研究,他的工作毫无功利性,最终却成为密码设置的试金石。《数字情种》告诉我们埃尔德什并不反对纯数学的应用,这一点和哈代不同。
我一直试图解释为什么埃尔德什的生命是有意义甚至是最有意义的。
人们总是强调科学的应用价值,这本无可非议,但不该仅限于此。在人类创造的一切事业中,唯有科学与体育的精神是一往无前的。科学的“认识论箭头”,在数论中反映得淋漓尽致。作为人类理性与智慧的最高象征之一,数论的价值远远超出了应用的范围。
数论中绝大多数猜想都异常艰难,那里没有金牌,只有世界纪录。也就是说,要在数论猜想中取得进展,不仅要和活人竞争,还要超越死人,这些人全都不是等闲之辈。一个数学家花费一年半载绞尽脑汁想出来的一条技巧,写出来往往区区几行,不要说外行,即便是内行也不一定能理解其中的辛酸和分量。
我以前的一位数学竞赛导师,是中国最优秀的教练之一。他从来不写文章,也不写书。数学家就是追求证明的美。花费大量心思把一个冗长的证明简化,再拿去发表,稿酬反而少了许多。这使我想起贾岛为了十个字整整花了三年工夫:“两句三年得,一吟泪双流”。最简洁漂亮的证明,同绝妙好诗一样,都是人类无与伦比的杰作。爱因斯坦对此深有感触,他说:“渴望先定的和谐,是无穷耐心和毅力的源泉。”埃尔德什则有一句最有名的口头禅:最好的证明都写在上帝的书上,数学家就是那些有幸瞥见一页半纸的人。这些话只有大师才能说出。由于数学是无穷无尽的,这一探索过程永远不会终止,生命也随之得到不断升华与常新。于是,埃尔德什就获得了连凯撒也享受不到的东西(据说凯撒掌权后,说道:“也不过如此嘛”)。
追求科学的至高真理,于大科学家还有另一层意义。霍金偶尔从心理上探讨过人们为什么对宇宙和宇宙学向往的原因。他认为,宇宙虽处在变化之中,但相对于尘世,其大尺度的时空结构还是能让区区几十年寿命的人感受到壮丽和永恒。宇宙学的定律,大概比社会科学模型长久得多。大科学家不是空间的主人,却是时间的主人。
爱因斯坦声称,他的世俗事务与科学研究两者毫不相干。这也是数学家的高明之处,他们缔造无穷无尽的抽象世界,与尘世并不冲突。数学家可以在现实世界与抽象世界之间自由走动,在现实世界中受挫,却以从抽象世界中获得安慰———“哦!原来有一个世界是完全可信的!”数学家的理想和现实之间的冲突从来就比文人的要小得多。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数学家享受到了更多的自由和幸福。埃尔德什穷尽一生在两个世界来回走动,并不感到有一丝疲惫。
从生活方式来看,埃尔德什既不传统,也不现代,他大概称得上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作为一个伟大的科学家,他和爱因斯坦一样,是人类尘埃中的恒星,可惜人们对他们的重视程度依然远远不够,这乃是充斥物欲和冷漠的社会所急需弥补的。
这些,也正是《数字情种》一书给的启迪。
